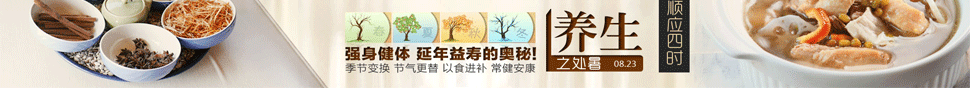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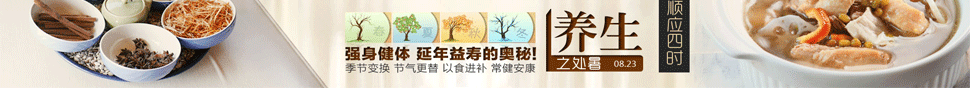
安安静静地聆听一些老故事,
内在的精神就长养了起来。
夏季的最后一天,
让我们搭个小板凳,就着一大碗茶水,
欢喜地听冯先生讲他的《果城旧事》。
鞋的故事
记得刚读南高那年,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就是下夜自习后的回家路。
我的初中是在白塔中学读的,因为是住读,所以没有集体上下夜自习的感觉。到了南高,学习节奏一下子变快了,其急促的鼓点就是几百人一起下夜自习后匆匆回家的脚步声。那时候涪江路是一条很窄的泥土路,晚上没有路灯。一放学,完全是南高的学子们,一路嬉闹着,争论着,流水一般向灯光灿烂的五星花园奔去,很是壮观。
学生是没有自行车的,再远也要走回家去。使今天南高学友想象不到的是,学生中起码一半以上几乎是全年光着脚上学的。那时中学生中拥有几双鞋的人凤毛麟角,我甚至不知道有没有人有一双属于自己的皮鞋。所以下了夜自习的脚步声其实是千百只光脚板的声音,踩得地动山摇,青春而勇敢。
我有一个男同学,过了几十年后老同学相聚,好几个女士不约而同地记得,当时在学校食堂吃饭,看到他穿一双白色网球鞋,遂悄悄认得了他。我这同学得意之下招认,当年确有此事,不过为了更加吸引女同学的眼球,他常常事先用白粉笔把鞋面粉刷过的。
当时南充有劳动工厂专门生产牛皮鞋。不过大约专门用于出口,很少有人看到过这种高帮皮鞋。南充还有一个布鞋社,生产布鞋在商店卖,但印象中我没有买过那里的鞋。我小时候穿的布鞋,最早是奶奶亲手做的圆口鞋,每年两双,基本上够我穿一年。奶奶去世后,市面上有了塑料底的布鞋,很结实,我们就穿时髦的塑料底布鞋,大多是成都产的。南充的布鞋大概比较晚才有塑料底子,不大记得了。
文革后期,社会开始流行塑料凉鞋。最早在南充风行的是飞机坝部队工厂生产的一种黄褐色橡胶凉鞋。不太贵,比较好买,穿起来比较柔软,所以老老小小很多人都穿。很快,各式各样的塑料凉鞋开始充斥市场,有了越来越多的颜色和样式,于是部队朴素的鞋就慢慢穿在了来自农村的光脚板上,转眼,农村也很少有人光着脚上街了。
终于,皮鞋摆上了货架,人们在社交场合不兴穿布鞋了。布鞋厂渐渐遭到和部队凉鞋厂一样的萧条命运。铺天盖地而来的鞋的大浪最后成了鞋的泛滥,这就走到了我们今天。今天,天价的鞋看上去和普通的鞋相差无几,最好的鞋看上去反而不大象鞋。而如果你高兴,在大学生们毕业离校的处理品中,和书一样多的也是鞋。
很多年前,人们公认布鞋是北京的好,皮鞋是上海的好。前几年,我专门请人从北京为家中老人买了两双棉鞋和两双圆口布底鞋。抚摸着这些黑土布为帮的老朋友,心中不免一丝久违的惆怅。
当年光着脚的南高学子们走到五星花园后就纷纷散开,走了自己的路。我有时还会和几个好友在五星花园逗留一小会儿,一包花生米或两斤才出的李子,打个小平伙,几个人在路灯下继续兴奋地聊一阵,然后各自回家,心满意足。此后数十年来,我时常满怀暖意回忆这些朦胧往事,知其不可再现,所以倍加珍惜。
打开水
其实我来南充的时候刚刚过十岁。六十年代初,家里不开伙,各在各的伙食团里搭伙。家里没得开水,要拎着温水瓶到街上“老虎灶”去买。可能是两分钱一瓶吧。
模范街那时候已经是全市最繁华的街道了,奠定其地位的主要标志是晚上有路灯。每隔大约二三十米,立上一根木柱头,挂一盏十五瓦的灯,比起没有灯的许多街道,已极显辉煌。街上有一个大一点的百货店,一个照相馆,一个水果店,再数下来,就要算是老虎灶了。
街口西头电影院旁边有一个很有名的“果园香”茶馆,上下两层,下面大堂里满是茶座,椅子和桌子都是竹子做的,好像用了很久,油光晃亮,乱七八糟布了一地,似乎还老满座。人进去得擦着墙边走,不然就挤不进里面的老虎灶打开水。老虎灶,很大很长很高,一字排开若干灶孔,上面各置一把大铜壶,亮闪闪地。开了一壶,长长细嘴里就会持续吐出激烈的白汽,把周围渲染得云雾缭绕。小伙计围着围腰,嘴里吆喝着,高举着开了的茶壶,跳舞一样在密集的茶椅之间摇摆穿梭,沏茶续水,可以做到滴水不漏,真功夫。
我那时喜欢去“果园香”打开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那里有一个小小的戏台,每每会撞上在上演曲艺。茶馆二楼是包箱,大约银子要多给一些,坐在里面一定比较宽敞,可以居高临下听戏,可我始终也没上去过,终于不知道美妙到什么程度。
在门口买个开水牌子(一个小竹片),一边就慢慢地往里蹭,眼睛却死盯住台子上的演出,或几个妙龄少女唱清音,或一个青春小生打金钱板,或一桌一椅一尺一老者演义评书,台下人声鼎沸,轰鸣灌耳,几乎只能以看代听。脚是不能停下的,不然要遭吼。渐渐地进到后堂灶间,老虎灶台阶上站一金刚师傅,十分威武。小心把牌子递上,水瓶高高地放在灶面上,退两步,看师傅一把特大茶壶略微倾斜,转眼就灌满了开水。折回,缓缓而行,眼睛再看舞台,台上依然在唱,台下依然轰鸣。
模范街仪凤街口也有一个老虎灶,灶当街而设,自然也有茶座,但没有戏文可听,属于极民间的茶馆,最多有几个掏耳人或修脚人在里边转悠谋生。我不得已时才去的。
渐渐,家里有了个时断时续的小煤炉,一尺多高,星期天放假在家,早上起来第一要务是将它端到院里,发火生炉,上放一壶,烧开,交代后便可自由活动。老虎灶就不去了,戏文也很少再听,不久,文革至,与茶馆一并扫地出门了。
待斗转星移,唯余茶馆矣。
头一回坐茶馆
过去南充的老茶馆很不少,凡有人群聚集处,必有茶馆,很具寄生性。
追究开去,大致和以下诸事有瓜葛。南充以前是很大的水码头,有码头就有茶馆,此其一;南充过去商业发达,有集市就有茶馆,此其二;南充过去文化教育之风颇盛,有文化就有茶馆,此其三;南充过去从革命党到哥老会风云聚汇,有聚会就有茶馆,此其四;南充明末以来为中原人入川大通道,会馆林立,有会馆就有茶馆,此其五。清中叶,南充城定格,东南西北四门间大小茶馆不知几许,至今还留痕迹。
像果园香那样的茶馆,在我小时候算是比较豪华的。大量的只是在一个大一点的房子里摆上很多竹桌椅板凳,木窗亮瓦,黑压压的大人们在里面喧嚣沉浮,搞些什么名堂我们一无所知,但觉得在那水汽和叶子烟味充斥的黑暗中,潜伏着多少大人们的未知故事。
隐隐约约觉得学校是不喜欢学生坐茶馆的,虽然也没听说过谁因此受了处分。所以当我大约初中二年级越过雷池、第一次去坐茶馆的时候,也还是受人教唆、事出有因的。那时候嘉陵江上没有桥,我们在白塔上初中,夏天涨大水,周日返校,等船往往要花好几个小时,同学们常常聚在码头上瞎聊。一回,班里一个要好的、大龄的、留级的学友胆大包天,阴悄悄带我登上模范街东口的“望江楼”。那是个二层的小茶楼,沿着叽叽嘎嘎的木楼梯上去,木楼板小房一间,设四五茶座,下午时分,竟空无一人。临窗坐下,可望见大江滚滚。伙计前来,一人面前一份盖碗茶,青花黄钉,很是清爽。铜壶一举,飞流直下,腾腾热气,直冲胸膛。胆怯中夹着极度兴奋,兴奋中饱含无名恐惧。兄弟二人闲话,激动崇拜,不知所云。没多久,眼见得渡江船过来,于是结账,大哥开钱,一毛。老板娘那高兴劲我终身难忘:她最是喜爱我们这等茶客,板凳还没坐热就开拔的东西。
不久就是文革,市面上茶馆遁去,银幕上却有“春来”茶馆。文革后,先有“前门情思大碗茶”,继有“老舍茶馆”为首掀起的茶馆文化,兴隆至今。南充茶馆业也早已野火春风,竞争白热,商家使出翻江倒海之术,弘扬茶文明。所幸茶客如云,横跨男女五代。
如今我走上一家家由地毯铺就描龙绣凤充满文化气息的当代茶馆,在绿色的树彩色的书和天籁般琴声的熏陶下,看着那些年轻英俊的BOY左一个“苏秦背剑”、右一个“蛟龙出海”的时候,还真是把过去给忘得干干净净的了。
冰箱和空调
大跃进时候有很多口号,都很通俗易懂。其中一句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时的人期望,如果大家都住上了楼房,家里安装了电灯电话,离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不太遥远了吧。后来,说这话的很多人都活到了住楼房用电话的年代。当然,社会还在前进,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还很远大。不过可见那时人们的生活质量实在很艰苦。很多人家住草房,或者是简陋的老式瓦房。六十年代南充上半城最有特色的房子要算如今延安路中段的一所两层楼房,是个邮电局。很多人家里没有电灯,点油灯。通讯主要靠喊,居委会主任有个铁喇叭筒,可以传播很远。
所以那时的人是绝对想不到把冰箱提到革命口号里的。和牛奶、咖啡、小汽车一样,冰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贴着资产阶级的标签。所以小时候我每每指着家里一件奇怪的家具,再三追问那是什么的时候,母亲总是支支吾吾说不明白。
很多年后才知道,那是一个非常老式的大约是上世纪初的冰箱。它大致是正方形的,有如今的小电视机大小,里里外外用几层金属皮包裹着,还有一个厚实的盖。据说还有些小部件,都不大重要。当时的人是在街上把冰块买回家来,放到冰箱里,再把需要冷却的东西也放进去,据说可以管几天。当然我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失去了原有功能,变做一个装杂物的箱子,搁置在很不起眼的角落里,无人问津了。母亲胆小,不敢提它的真实身份。
八十年代早期,人们首先抢着购买的家电是电视机,一个家如果有台黑白电视机,就是先富起来的象征。冰箱也进了商场,大多是外国制造。但那时的人们忙着填饱几十年没有塞满过的肚子,还来不及有剩余物资往冰箱里放,所以买的人不多。大约是八四年,南充市面上有了一批原装东芝冰箱,我家还没有电视机,就超前买了一台回来。冰箱是苹果绿的,很美丽,但是有一点六五个立方,我觉得实在是太大了,哪有那么多东西放啊,差点就不想买了。买回家来,很多人来看稀奇。我们兴致勃勃忙着做冰糕、做冰块,兴奋了好一阵子。两口子还盘算说:过去弄好的饭菜过不了夜,浪费大,现在好,一次可以煮一大锅,放在冰箱里,吃上一个礼拜。外国人过日子也不过如此了。
渐渐,国产的冰箱越来越多,紧跟着电视机的脚步,冰箱和洗衣机、电话以及世纪之交的电脑、手机都大踏步涌进了百姓家庭。现在很多小孩子从生下来就知道使用冰箱了,没有冰箱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市面上的冰箱琳琅满目争奇斗艳,有透明的,有闪烁金属诱人光芒的,有惊人节能的,有迷你型的,实实美不胜收。今年世界杯期间,我在电视上看到,德国商家在冰箱宽大的肚子上开个口子,专门制作生啤酒和冰啤酒,供可爱的德国球迷同饱眼福口福。当时我就想,我们也可以开口子,做冰豆浆、冰乌龙茶,还可装上小音箱、小电视甚至小电脑,那该是多么快乐的厨房啊。我看,这个时代恐怕不会太远了,我们等着换多功能冰箱吧。
空调是我们几十年前听也没有听说过的东西,其实和冰箱在技术上大致差不多,主要差别是一个人在里一个人在外。几年前,我和同事在武汉参观东湖,才知道五六十年代中央政治局也没有空调,夏天的武汉很热,专门在会议室两侧安装了放置大冰块的漏斗,开起会议来要用大电扇把冷气往屋里猛吹,又象空调又象冰箱。现在想想,觉得这世界的脚步实在是太快了点了。
说吃
如今五十来岁的人,说起童年的记忆,十有八九和吃有关。儿时哪怕在树上摘了串槐花塞进嘴,那味道都可以陶醉到今天。那个时代,民以食为天。
小时候,川北凉粉、南充冬菜、张飞牛肉等都不是我们所知道和所期待的。南充最大的馆子是五星餐厅,地点在五星花园。五星餐厅最使人流连忘返的是麻辣面,二两一碗,用上等蓝边细瓷碗端上来,红油海椒上撒些花椒胡椒面,鲜鲜地供上一撮炸得焦黄的肉颗颗,一望就口水长流。六十年代初,南充出现三样吃的,一是小蛋糕,属果园香的好;一是抄手,邮电局对面开张一个小店,极盛;一是锅贴饺子,为一东北老汉所传。在下只要手里有几个铜板,都是迫不及待地贡献了的。
若钱少,还有几个地方可光顾。禹王后街有个名字很洋气的饭馆叫“果尔佳”,其实卖稀饭、咸菜和包子,但鸡丝面是绝活;模范街口有个奇怪名字的店叫“二五八”,卖甜醪醩和小汤圆。初中毕业那年,我们大多星期天早上才回家,过得江来,常在那里打平伙。
说起中学时代,实在惭愧,简直没沾几点油腥。八人一桌,围桌而食。“席长”手里拿把竹刀,操分饭大权,均分一脸盆饭为八份。半月见一次肉影,从上午第三节课起就心神不定,满教室骚动。待中午的下课钟声终于响起,孩子们从教学楼里奔涌而出,翻江倒海“打牙祭”去。节日啊!席长在众目睽睽下把十数片肉均分进八个碗,那是很神圣的事情。所以初中很有地位的人可当选席长,我曾积极争取,竟无此殊荣。
童年的友谊很真挚,你有我有全都有,和最要好的朋友在高坪场上买麻花吃,至今不能忘怀。另一回,斗胆奢侈叫一份鱼肉丸子来,说是肉,其实头尾刺全在,连着友谊一起下肚,乃记忆中一桩少年豪举。
上面只是些关于吃的皮毛。真要说吃,学问就很深。有以为人有了身份就不宜言吃,谬矣。正相反,许多自以为有身份的人,如果只会吃,不懂吃的道理、吃的做法、吃的典故、吃的习俗,则是浅薄、无聊和没文化。吃文化、酒文化原本就是中华大文化的一部分,源远流长,奥妙无穷。远的不说,清朝大文人袁枚,不但积数十年写过著名的《随园诗话》、《随园随笔》,也留下非常有讲究的《随园食单》。清朝另一文豪曹雪芹写《红楼梦》,如果以食谱和茶道论,也颇高深门道,足可使今日诸食客们汗颜。
人的口味常和生活地域有关。八十年代以来,南充餐饮日渐兴隆,由饭馆饭店而大饭店大酒店雨后春笋一般争相比美,有几个符合大众消费的馆子也相当火爆,一些火锅店时常要等二轮、三轮才吃得成。西餐、粤菜也曾一时登陆,可是潮起潮落,南充人还是最喜欢川菜,即使要变,也得貌离神合才站得住脚。
至于个人在吃方面的特殊喜好则往往由历史偶然造成。初一时,我的下铺年长我,家里开着锅盔店。周日返校,夜来人静,总要悄悄塞半个到我嘴里。躺在铺盖里,一口口细细享受,其乐无穷。所以几十年来,偶尔有人席间问我食之最爱,我还是朗声答曰:“锅盔”,坦然面对满座的惊奇和竊笑。
再说吃
现在提倡挖掘饮食文化,很有道理。比如阆中几样饮食:张飞牛肉、蒸馍和醋,论文化就很值得一挖。以我猜,大约都和清兵入川时长期驻守阆中有关。牛肉和馍是行军打仗的干粮,方便、经饿,很像压缩饼干,多半是西北旗人带来。此话未加考证,只图说明有些饮食也许有很深的源头。
川北凉粉是南充人的自豪,想来也有道理。做凉粉的原料本来很多,比如红苕。白露后,陆续从地里挖来,越挖越多,吃不赢了,就没日没夜推成苕粉保存下来,待节日来客,做成凉粉,拌上自家佐料,很卖座。豌豆也是川北主粮,做出的凉粉白嫩嫩的,和黑呼呼的苕凉粉比,有如小姐和丫环,遂成名入市。另一种粉是米粉,南充人说比云南过桥米线还好吃。许多从南充的大学里毕业到五湖四海的学子,聚会天涯海角,无不怀念南充米粉。米粉最早以羊杂汤为主,说不定也是从西北进来再本土化了的。但奇怪的是,这米粉竟只能在南充卖座,即便是在包容性很强的成都,也似乎很难施展开拳脚。
有些饮食已经很难见到了,其中有米豆腐。米豆腐用碎米加工做成,一坨一坨黄灿灿的,买回家来,用腊肉蒜苗炒出的为荤、炕成二面黄撒几颗椒盐的为素。倒转去三四十年,南充人都很爱吃,大约太民间,如今已无人问津了,可惜。
南充原来还有些小吃也很值得留恋。比如说“葱(读四声)”。我们读南高时,下了夜自习,往往乘机到五星花园繁华闹市转一圈,大多喜欢去围卖“葱”的摊摊。那摊摊,用一马夹支起,上搁一块小枱面,铺上雪白的布,几个小碗小碟置备好红油、酱油、味精、葱花、花椒胡椒面,样样精神抖擞。用手取一张薄薄的面皮,飞快地在各式佐料中掠过,然后再用小勺从一个瓶(或罐)里取几滴绿色浆末放入,灵巧地包成一个三面封闭一面开口的“葱饼”,递过来。你接手后须赶快一口下肚,不然要漏。这一口才下去,马上就七窍大开,眼泪鼻涕一齐喷射。但是,要就要的这个感觉,特刺激。摊摊的“葱”各有秘诀,据说有用油菜籽做的,有用青菜籽做的,各有神通。学生们各有喜爱的摊,如同今日追星族,场面很是可观。
再早些年,南充还有豆浆挑子,一头是个盛豆浆的小木桶,一头是些佐料,也用白布盖着,架上挂一盏油灯,走街串巷。那时没有糖,以糖精替代。豆浆挑子大多要吆喝,在寂静的夜里,那调很古老、很苍凉,今已失传。
四川人每说南充,有一句话,说是走到西山坡,就可听到南充人民喝稀饭的声音。此话若反听,是说南充人穷,只配喝稀饭,比如当年广安来接我们下乡的李书记自豪地对我们说:我们广安,那,顿顿都吃干饭!激励我们义无反顾投奔他的麾下。此话若正听,是说南充的风俗。既爱喝稀饭,就讲究下稀饭的菜肴。南充人喜爱用泡咸菜下稀饭,许多人家里大大小小好几个泡菜坛子,菜泡得好坏主要是盐水起的水平,菜用些时令菜,春泡青菜、夏泡豇豆、秋泡海椒、冬泡萝卜,稍微富贵一点人家的菜坛子里,还可以捞出嫩姜、洋姜什么来。喝稀饭的时候,普通人家拈两块咸菜在碗里就可以端着碗左邻右舍地去串门了,庄重一点的,需要围桌坐下,几碗咸菜端上,再配一两碟干咸菜,甚至于炒一碟豆腐干、二两花生米,那算得上是很正规的饮食了。
作者简介:冯文广先生,汉族,年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人文学者。年毕业于西华师范大学,教授,硕导,人文学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高校教育、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历任川北医学院党委书记、成都理工大党委书记、四川省政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侨联主席等职。现居南充。
嘉湖书院于南充,
有着深长的意味。
当一座城市有了一家书院,
在人世间就不会被风吹散。
如果你有值得的故事,
如果你有生动的诗文,
记得投稿《嘉湖文苑》。
邮箱:
QQ.

